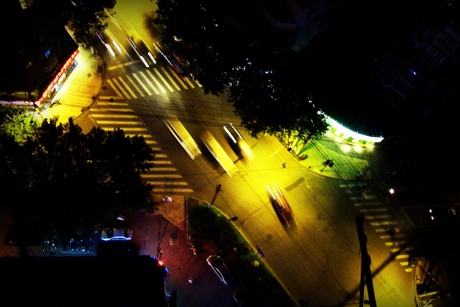尽管现如今商业极其发达,尽管北京和上海是中国大陆毫无争议的最大的两个城市,而且相隔只一夜火车或两个钟头的飞机,仍然有很多的食材只能在上海买到,而在北京买不到。
例如,北京买不到竹笋。今年春天在北京的时候,发了疯的想吃腌笃鲜。腌笃鲜其实是极其容易的,自己家里就能做的:新鲜的猪肉(比如肋排),咸猪肉,还有笋,加上佐料(比如葱段、姜、黄酒、盐等),放在大锅子里煮开,然后小火炖上至少两三个小时,整个房间里便香气四溢,揭开锅,厚厚的油花满锅的笋片,根本不消吃,只要想到,就口水流下来了。只可惜,在北京,这个春天满世界找不到笋,无论是细长的春笋还矮矮胖胖的冬笋。当然,我的“世界”仅局限于晚上七点以后的白石桥家乐福(//shy)。据北京当地人说菜市场有时候会有,但我并不知道德外附近哪里有菜市场,只有那次去玉渊坛公园看樱花,在公园门口的一溜小摊里看见一个挑着竹笋卖的。当时一犹豫,不想拎着一口袋竹笋看樱花,就没买,后悔啊。
我在北京时还想做马兰头拌香干。典型的江南小菜,把豆腐干和马兰头(一种蔬菜)用水汆熟,剁碎了拌在一起放盐、味精和麻油就可以了。可是北京也买不到马兰头。
北京也买不到芨菜,做不了芨菜豆腐羹。大部分的菜肴,饭店里做的比家里自己做的好吃,毕竟饭店是专业的,而且饭店里油大、火旺,有些还用高汤,这都是自己家里不能有的条件。但有个别的菜肴,饭店的反不及家里自己做的,例如荠菜豆腐羹,还有腌笃鲜。饭店里的腌笃鲜绝对不如我的手艺好,这不是吹牛。饭店里因为成本考虑,用的原料不如自己家的足。饭店里的腌笃鲜往往清汤寡水,笋也少、肉也少,汤也非原汤,是兑过的。
八宝饭也是自己家做的好吃。只可惜我妈妈已经有十几年没自己做八宝饭了。以前念小学的时候,到了寒假,农历十二月二十几的时候,我们就在家自己做八宝饭。在桌上一溜摆开大大小小十几个瓷饭碗,碗壁和碗底都先用猪油抹一遍(否则将来蒸熟了沾碗),然后在碗底摆上各种蜜饯,比如核桃仁(从食品商店买了大核桃自己敲的)、糖冬瓜、蜜枣、等,大多摆成放射状。摆蜜饯通常都是我的工作,一边摆一边还可以偷吃一些,但我不喜欢吃糖冬瓜。另一边,用高压锅煮糯米,然后先在每个碗中盛一半的糯米,压实;然后铺上一层豆沙(自然也是自己家炒的),压实;最后再铺一层糯米,压实至与碗口齐平,就算做好了,那去垒在阳台里。等到小年夜开始,年夜饭就不吃白米饭了,而是从阳台拿一个八宝饭,从开始吃前面的冷菜和热菜开始就上锅蒸,等菜吃完了八宝饭也蒸透了,取出来倒扣在一个盘子上,揭掉碗浇上一层甜的芡就很美味了。
北京人很少吃八宝饭,因为八宝饭太甜:糯米是甜的,豆沙是甜的,蜜饯是甜的,浇的芡也是甜的。而且,北京的家乐福里面卖的八宝饭无论怎么蒸,米粒都不糯,怀疑是用大米做的。
除了八宝饭,那时侯过年我们家蛋饺也都是我姐做的,从蛋皮到肉馅。现如今,都直接买现成的了,买个乔家栅的八宝饭放在电饭煲里一蒸就当午饭吃了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