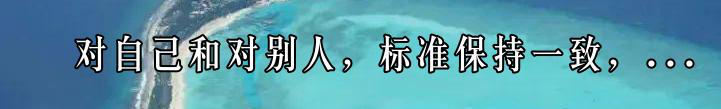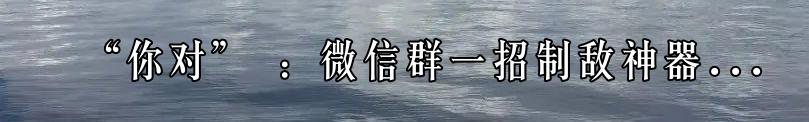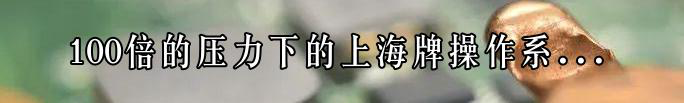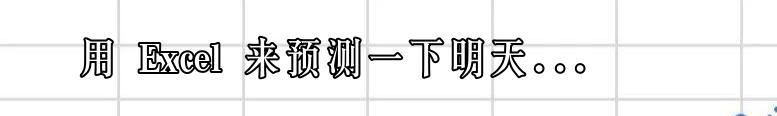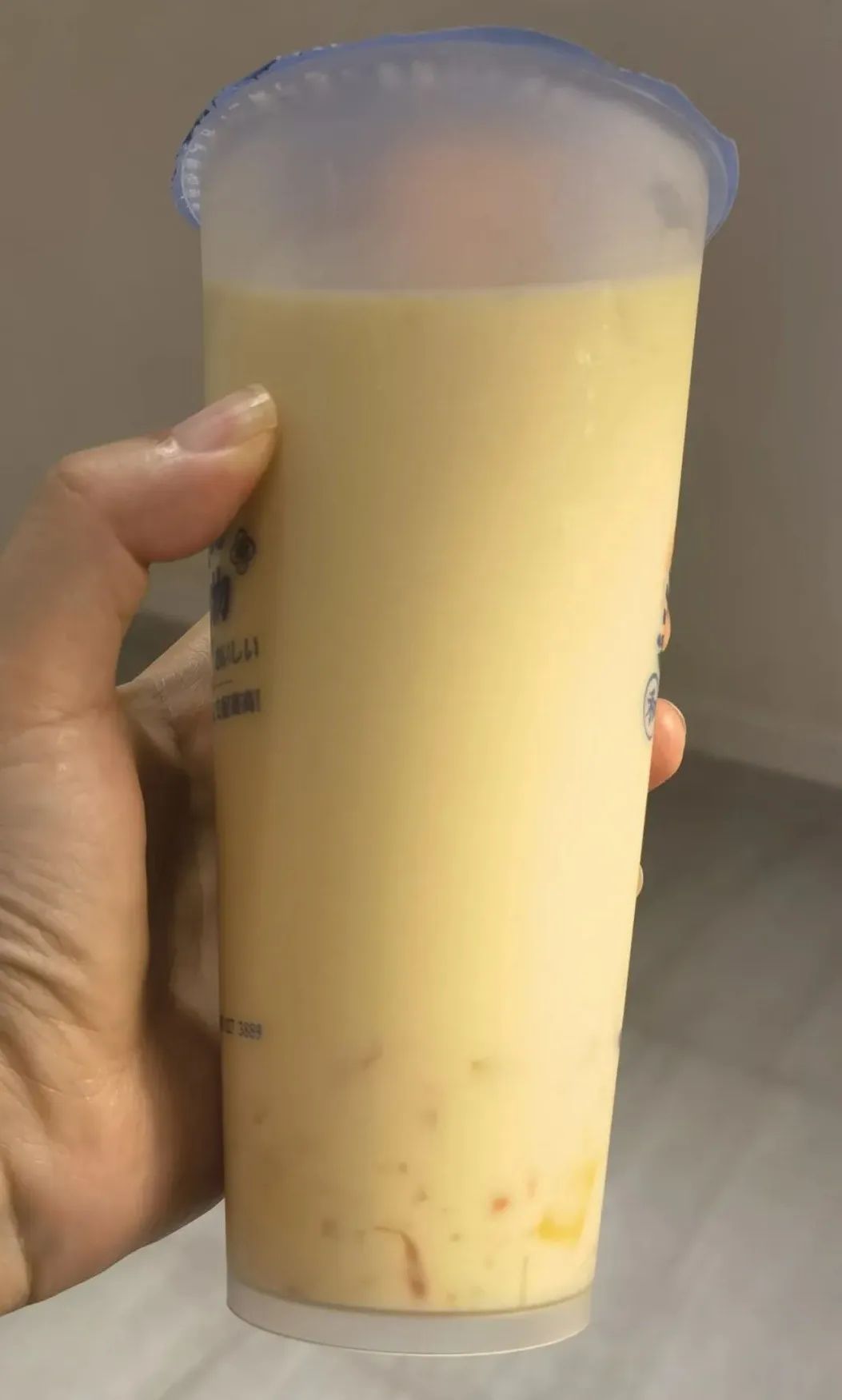规则就一定要遵守吗?
这是一个会给回答者带来风险的问题。
如果不假思索,给出的答案将是肯定的。
但如果真的如此执行,不出 24 小时就会被现实的种种矛盾击败,尤其在封控中的上海。

混乱的规则下讲规则的人的困境
我喜欢的上海,就是一个讲规则的社会。大家看中规则,发现不合理的规则会去抗争,对于好的规则极力遵守。
一个疫情下,上海的形象一落千丈,无数带着 bug 的规则从天而降,让习惯了遵守规则的市民一下子蒙了,虽然也依然和不对的规则抗争,遵守合理的规则,但短时间产生的混乱无法避免。
对于坏的规则,这座城市里的人们怎么选择呢?
有人选择了遵守规则,即便它是错的;有人选择了用不遵守规则作为反抗,就如同我们小区的几位英雄对抗楼下的铁栅栏一样。

不管怎么说,两种做法各有各的道理。但有一点是确定的,这个答案,短期无法达成一致。
就如同在平时,天上掉下来个 1+1=2, 和 1+1=3,大多数人能够一致的选择前者,社会运行平稳,井然有序。
但是如果这个时候,天上没头没脑地忽然掉下来 1 ,和 2 两个选择,让人们怎么选?因为没有参照物,选 1 的和选 2 的都为数众多,这本身在所难免。
无论大家做什么选择,都可以理解。但真正重要的,不是个人的选择,而是个人对其他人的选择的态度。
如何看待别人的选择
我观察到,作为一个城市,大家对于别人的选择的态度,不一致,多变,矛盾,且不自知。
在各种事件中,如哲学家一样稳定地维持着自己的标准和理性的人不多。在不同的情境下,我自己反思,也经常用不同的标准,矛盾的理论,做出变色龙一般的反应。
举个简单的例子。疫情早期的时候,在悲情的情境下,大家对于强制老人转运方舱的事件,未成年母子分离转运的事件,对于因为防疫要求无法及时进入医院耽误了治疗的事件,在网上疾呼。
我们痛恨那些冰冷的规则,痛斥所有僵硬地执行规则的人。那些规则,是所有人面前软弱的靶子。大家尽情地谴责,把能找到的最大的石头投掷到那个靶子之上。
而一旦到了自己的身边,似乎规则的地位又忽然提高了很多。当会影响封控的时间的时候,同样的规则又成了坚硬的盾牌,用来保护着自己的利益。
大家一边痛斥足不出户的规则毫无科学根据,一边更加猛烈地痛斥不遵守这一规则的邻居,拍照片发到群里面,打电话去投诉和举报;
大家一起批判每日核酸的必要性,又要求邻居和自己一样去做核酸,以免影响解封,虽然这种呼声从第一天到现在越发软弱下来。
更有趣的是,在群里面强烈地批判邻居违反封控区足不出户规则的,自己却大摇大摆地在小区里面散步,跑步或者取快递。
他们在要求别人遵守规则的时候,又化身维护规则的正义斗士;在自己不遵守规则的时候,化身反抗规则的正义斗士;在检举揭发邻居的时候,又变成维护规则的正义斗士。行为一百八十度的翻转,内心却依然认为自己是正义斗士。
如此看来,疫情期间的各种争论,哪有那么多流派,基本上只有两派,就是允许自己做,也允许被人做派;允许自己做,不允许别人做派。除此无他。
乱世中难得的体面
我也看到很多沉默的大多数,他们的选择自始至终一致调和且一致。
他们对于规则自己做了选择。
无论他们认为规则是正确的,还是错误的,他们自己的选择是遵守,还是不遵守,他们至少对其他的人保持了同样的标准。甚至还有更难能可贵的,无论自己的选择如何,都对不同选择的邻居给予善意和包容。
对自己和对别人,标准保持一致,而不是双标,是乱世里一丝难得的体面。







 。
。